凌晨三点的寂静,像一块沉甸甸的铅,压在城市上空。女儿的哭声在耳畔撕咬,我抱着她在飘窗前来回踱步,木地板被踩出细微的呻吟。
月光清冷,透过窗棂,将暗影投在她稚嫩的小脸上。那些红疹子密密麻麻,像碎了的石榴籽,看得我揪心不已。台灯下,已经换过的第四支药膏泛着青白的光,无声诉说着这段日子的焦灼。自从女儿患上顽固湿疹,这样的深夜拉锯战,已经持续了整整二十八天。
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起来,震得玻璃杯里的半盏凉茶泛起细小的涟漪。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刺破黑暗:“你爸今早摔了碗,说左眼像蒙了层黑纱,看不清东西……”我低头望着怀里刚睡着的孩子,突然觉得整座城市都在摇晃。窗外的路灯成了悬在空中的萤火虫,明明灭灭,恍如我此刻飘忽不定的心绪。
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多年前的夏夜,母亲也是这样抱着高烧的我,在急诊走廊上奔走。39.5℃的高烧把我的记忆烧得模糊,只记得她棉布衬衫前襟的纽扣硌着我的脸,消毒水味道里混着她鬓角的茉莉头油香。
此刻,女儿滚烫的额头贴着我的锁骨,那点温度穿透皮肉,直往心脏里钻,恍惚间竟分不清是五岁孩童还是四十七岁的我在承受这份灼痛。
省立医院住院部的电梯,总在十三层停驻。当电梯门缓缓打开,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,我的心也跟着揪紧。父亲蜷在蓝白条纹的被单里,像片被虫蛀了的枯叶,脆弱得让人心疼。护士掀开他眼皮检查时,我瞥见床头柜上半块没啃完的苹果,氧化发黄的切面让我想起老家院角那棵歪脖子树。小时候我出水痘,父亲就是蹲在那里削苹果,果皮连成长长的银河,父亲说这是能带走病魔的流星。
手术同意书的钢笔尖洇开墨渍,在纸张上晕出黑色的泪痕,仿佛是我内心焦虑的外化。走廊尽头传来女儿的哭声,妻子正抱着她躲开消毒推车。小丫头伸出裹着纱布的小手,要抓我的衣服,药棉蹭在衣襟上,像开了一串苍白的梅花,刺痛着我的眼睛。那一刻,我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。
深夜,等女儿终于沉沉睡去,我翻开家庭相册,泛黄的胶片里藏着时光的足迹。抱着刚满月的我笑出酒窝的母亲,鬓角还没有那缕银丝;扶着自行车教我骑车的父亲,后背尚未被岁月压成拱桥。此刻的视频通话窗口里,他们正笨拙地学习用智能手机拍下孙女的新疹子,镜头晃过餐桌,我看见三个搪瓷碗盛着一样的降火汤,那是他们默默为我准备的。
今早给父亲滴眼药水时,女儿突然摇摇晃晃扑过来,把湿疹膏抹在爷爷手背上。老人用尚能视物的右眼凑近那管药膏,忽然笑出眼泪:“你小时候不肯吃药,你妈把药粉藏在龙眼肉里……”话音未落,小丫头抓起桌上的龙眼,举到爷爷的嘴边。
时光仿佛在此刻重叠,过去与现在交织,生命的传承与延续在这温馨的一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窗台上的绿萝在疯长,气根沿着我捆扎的棉线向上攀援,充满生机。母亲在电话里说,老宅的龙眼树开花结果了,父亲用术后尚在恢复的眼睛,数清了已结出的十八颗龙眼。女儿脸上的红疹终于开始结痂,清晨的阳光里,她脸上那团晃动的光斑渐渐化作了蝴蝶的形状,仿佛预示着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。
昨夜哄睡小丫头后,我摸黑到厨房倒水。月光突然涨潮,漫过大理石台上并排的三只玻璃杯——父亲手术后忌口的蛋白粉,女儿抗过敏的氨基酸奶粉,我自己凉透的枸杞茶。三种不同的颜色在月色里轻轻碰杯,发出唯有中年人才听得见的清响。
这清响里,有责任,有牵挂,有疲惫,更有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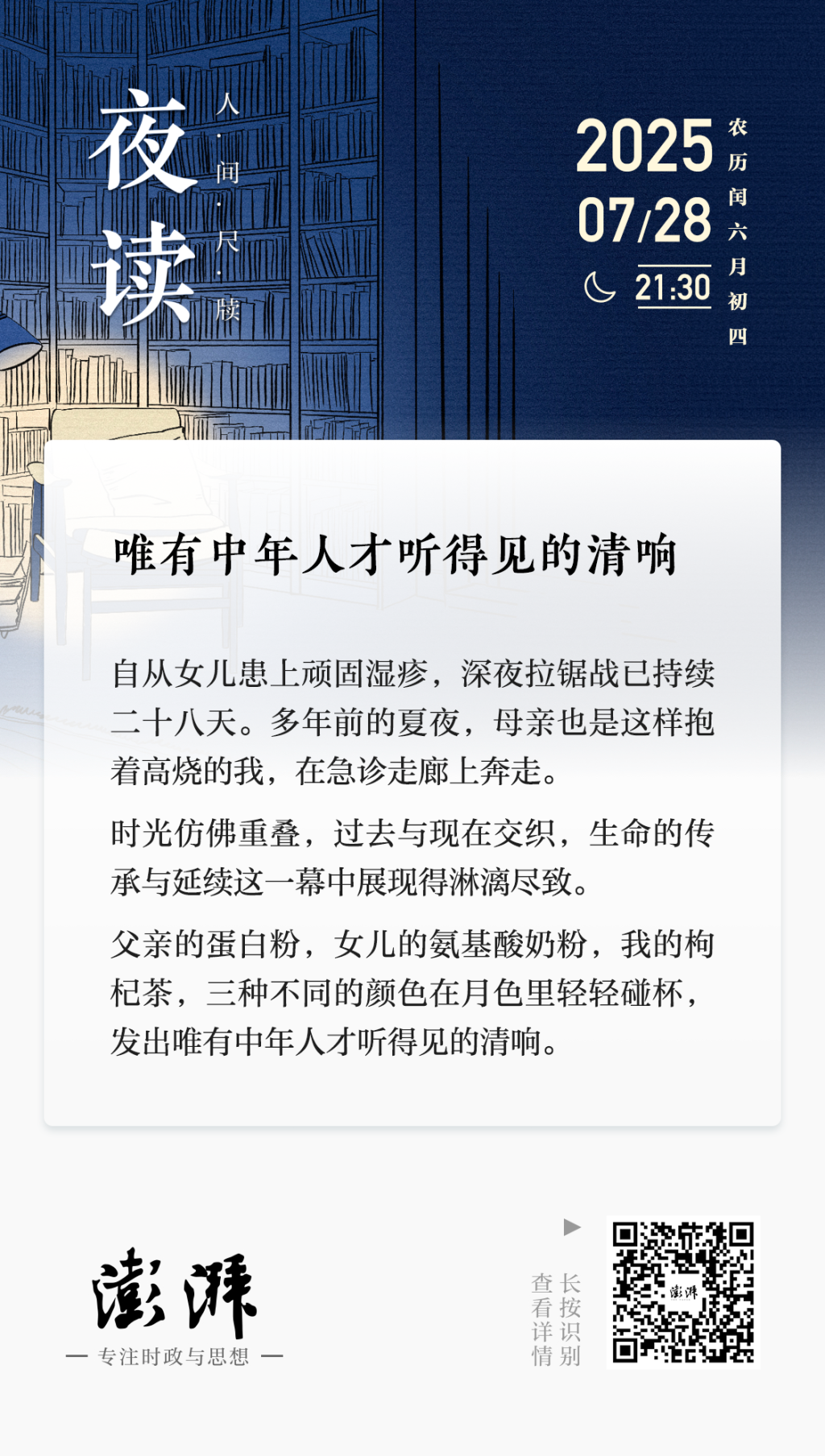
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,本文标题:《夜读|唯有中年人才听得见的清响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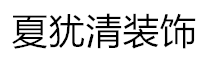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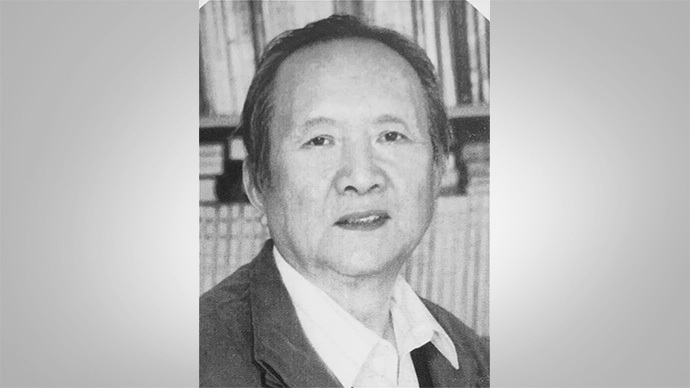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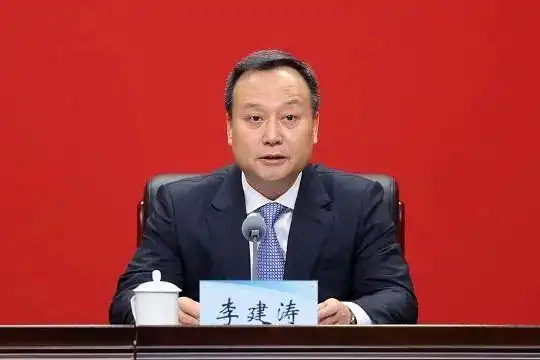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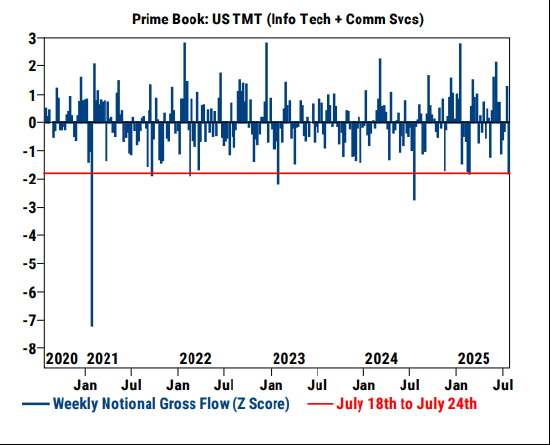




 京ICP备2025104030号-12
京ICP备2025104030号-12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